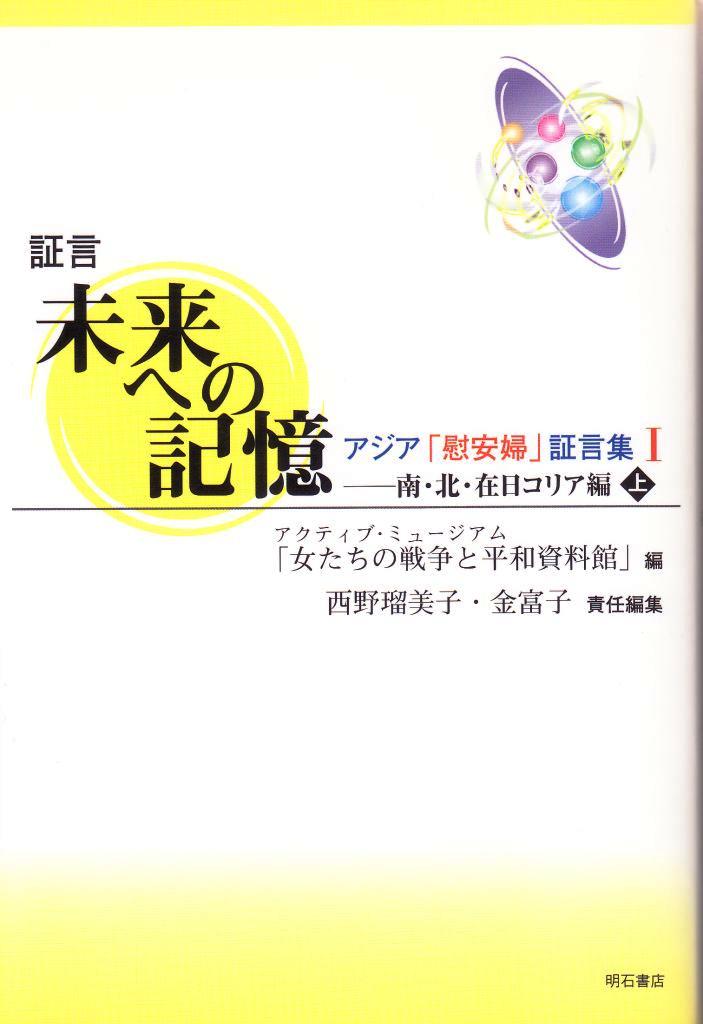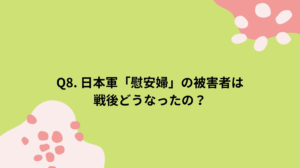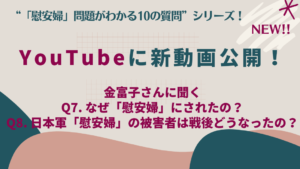A:“作证的时候转移了话题”、“未提及受到陆军、其他政府机构的强制性劳动”(“THE FACTS(真相)”2007年6月14日)等等,有人提出了否定受害者证言的主张。但是,能够断言“因为没有当初的证言就没有那个事实”吗?还有,能说“因为转移了话题,证言本身就不可信了”吗?在此,我们来看一下受害者证言的取证方式。
1、记忆和创伤
首先,度过全部证言后我们能说的是的确受害妇女的证言中在“何时”、“何地”、“什么人”等方面有些模棱两可的地方。以中国、东帝汶的受害妇女为首的受害证言中,甚至有连自己的出生日期都不清楚的情况。还有虽然知道是被带到中国,但不记得具体地名这样的情况。
例如,文必璂是被装上火车带到慰安所的,虽然她记得是经过新义州进入“满洲”的,但是自己被带到的慰安所所在的地名、使用该慰安所的部队名都想不起来了(活动家博物馆“妇女们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编《证言 面向未来的记忆 亚洲「慰安妇」证言集——南・北・在日高丽人篇・上——》明石书店2006年P165~P177)。
但是,像对慰安所的详细讲解、很多日本士兵过来、军人在慰安所站岗放哨、如何被带过去的等等事情,她又令人吃惊地记得非常清楚。正是在详细讲述“发生了什么”的过程中,有那种永远无法忘记的伤痛和痛苦的感觉。虽说一部分记忆遗漏了,固有名词记不起来了,但不能就因此说证言全部都没有可靠性而舍弃。
记忆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有时会忘掉。例如,处于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下加上身为女性,朝鲜妇女完全上不了普通学校的比例在1932年达到91.2%(金富子《殖民地朝鲜的教育和性别》世织书房2005年)。由于不能充分地接受学校教育,很多女性不识字,所以她们不能通过文字,而不得不依靠耳朵听到的声音来记忆。在听取受害妇女的证言时,必须要了解这种情况。
还有,记忆的不完整以及记忆的消失,也说明了妇女们所受到的巨大伤害。关于记忆的不完整,精神科医生桑山纪彦解释说:“尽管一个一个的记忆非常清晰,但是有之间的交替、或者时间上的前后联系弄不清楚的现象。”关于创伤的实际状态,他还指出:“说的就是人们在经历一件事情时,遭遇了那种产生显著痛苦、打碎生存希望、破坏重要人际关系、几乎觉得再也不能恢复之类的事件,心灵受到伤害的状态(桑山纪彦“原中国「慰安妇」的心灵伤害和PTSD”《季刊 战争责任研究》第19期、1998年)。
朱蒂斯・刘易斯・赫曼指出,这是受创伤人的外伤症状的记忆特征(朱蒂斯・刘易斯・赫曼《心理创伤与恢复》三铃书房1996年)。刚开口时,受害妇女还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创伤,说出被认为是不合逻辑、没有条理的证言是一种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但是,她们在“会有人认真听取自己的证言”这样一个有“安全保障”(在回忆与服丧追悼、再结合的共同恢复过程的一种)的环境中,已经冻结的记忆就会逐渐解冻。
进入90年代,妇女们打破沉默开始述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按照赫曼的说法,这也是一个“恢复过程”。有人能够毫无恶意地倾听自己的经历,这种环境的变化可以说是向伤害恢复敞开大门的一个契机。那些说妇女们的证言“是捏造的”“想要钱而撒的谎” 等等,只进行攻击的行为,无非是对受害妇女再次施暴而已。
2、如何看待金学顺的证言?
屡屡有人举出“在提起诉讼时的诉讼书中所写的被征召状况和之后的证言有出入”、“隐瞒了妓生(类似艺妓)身份”等说法来否定金学顺的证言。例如《慰安妇和战场上的性》(秦郁彦著)中登载了“金学顺证言的异同”的表格,其中“f 被迫当慰安妇的情况”中分别列出ABC三条“被征召”的证言,但是细看的话就知道并没有矛盾。A写的是“在北京的一家餐馆,被日本军官怀疑是间谍,和养父分开,(我)就这样被装上卡车带往慰安所…”;B写的是“和A相同”;C写的是“日本兵胁迫养父,(将我)强行带往慰安所…”。要举出这里面“异同”的“异”的话,就是“养父受到胁迫”的部分。但是可以说在“怀疑是间谍”的交锋中“养父受到胁迫”,完全不是矛盾的证言。而且,被迫和养父分开的金学顺被日本兵装上卡车强行带往慰安所肯定是事实,所以不能说和作证时的内容不符。在多次的证言中,也会有些被突然想起、逐渐清晰的事情。虽说最初的证言中不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全面否定证言。
另外,被迫当「慰安妇」的妇女和是不是妓生没有关系。强行将人装上卡车带到慰安所的行为就是“强制征召”的问题。假设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养父将她“卖”给军人的话,日军就涉及到未成年女性的人身买卖。这样就是违反当时刑法的犯罪行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刑法第224条“未成年人略取及诱拐”中规定禁止略取或诱拐未成年人,刑法第224条“以营利为目的的略取及诱拐”中规定禁止以营利、猥亵或结婚为目的略取或诱拐他人)。
3、《河野谈话》以及历代首相都承认了“证言”中所反映出来的强制性
《河野谈话》承认了「慰安妇」征集和慰安所具有强制性。发表《谈话》的河野洋平就其理由听取了16位受害妇女的证言,他说:“只有明显遭受非人待遇的人才可能说明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出现,由此可见,这些证言是有可信性的。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可以说都是值得充分信任的(为妇女说话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口述历史 亚洲妇女基金》2007年3月)”。
自桥本龙太郎首相包括第一次安倍内阁在内的历代首相都沿用了河野谈话。作为承认“强制”的说明,政府答辩说:“据政府调查的文件中找不到显示军队、官府强制征集慰安妇的记述。综合判断的结果,认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可以说,历代政府也是承认受害者证言的。
4、不是由受害妇女来证实责任之所在
最初,在受害妇女的证言中寻求“你自己被关进来的慰安所由谁管理和监督,在谁的命令下开设的,是谁命令将你们带到那儿的”等事实关系上的证据,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就算直接欺骗她们的是警官、区长、经营业主,但是是谁指使他们征集的,她们也没有理由知道谁是“主谋者”或“命令者”。
虽说在受害妇女的证言中没有出现责任的主体,但是也不能说事实不存在。要说通过受害妇女们的各种证言要弄清楚什么(探明真相),不是受害者而是日本政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