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首相声称:没有“官方警察闯入家门像人贩子那样把人带走”的“强制性”行为(2007年3月5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大坂市长桥下彻也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慰安妇」是‘受到军方的强制胁迫’而被带走的”(2012年8月21日记者招待会)。
无论是安倍首相还是桥下市长都主张:如果不同时具备①由军方・官方警察(执行),②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法律用语称为强掳)这两个条件的话,就不算是强行征召。这其中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日军在朝鲜、台湾召集女性的时候,会选定相关的业主,让这些业主去召集(也有军方委托总督府去选定业主的情况)。这些业主被称为“女衒”,平日里从事一些人身买卖、诱拐(使用欺骗、密语哄骗进行征召)等勾当,因而他们在召集「慰安妇」的时候也常常采取了同样的方法。
上述情况都是违反刑法第226条的犯罪行为。而且,所谓强制,是指违背本人意愿而实施的行为。因此,诱拐就是强制征召行为。人身买卖对于(被征召者)本人来说也是经济上的强制行为,所以也应该说是强制征召。通过诱拐、人身买卖征召来的女性被关进军方设施「慰安所」里,被迫成为军人的性对象,是一种强制驱使行为。在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中,军方负有重大的责任。如此简单明了的事实,无论是安倍首相还是桥下市长,他们都不愿意正视。
有关朝鲜、台湾的女性被以诱拐、人身买卖的方式带到国外的证据,除了受害者本人的证言之外就再也没有了吗?并非如此。这样的证据有很多,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看。
首先,有美军的资料为证。这就是由二战期间美国情报局心理作战班制作而成的,在当今非常有名的《日本战俘审问报告》第49号(1944年10月1日)。对于为数众多的朝鲜妇女被使用诱拐、人身买卖的手段带到缅甸的情况,在该报告中有如下记载:
一九四二年五月上旬,为了在被日军新征服的东南亚等地征召从事“慰安劳务”的朝鲜女性,日本的一些淫媒业者来到了朝鲜。虽然没有明确这种“劳务”的性质,但是人们都以为其职务是照料医院的受伤士兵,给他们包扎一下绷带,更通常的想法是把它当一项能使官兵开心的工作。这些淫媒所使用的说辞是:‘可以挣很多钱’,‘是偿还家庭债务的好机会,而且,拥有轻松的工作和崭新的天地—-在新加坡的新生活具有光明的前途’等等。正是由于听信了这些虚假的说辞,许多女性应聘了去国外的工作,收取了二、三百日元的预付款。(吉见义明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资料99,大月书店)
这种做法构成了移送国外目的的诱拐罪。而且,因为支付了200-300的预付款,又构成了移送国外目的的人身买卖罪。美军的这个记录中还记载到:“大约有700名的朝鲜女性被骗去应聘,在之后的6个月至一年期间,被军方规定以及淫媒业主的劳务所束缚,在规定的劳务期满之后也要被迫重新续约”。对此,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以军方为主犯,业主为从犯的犯罪行为。如果说这不是强制征召又能说是什么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关于被诱拐带到缅甸仰光慰安所的朝鲜女性的记录。以下是原读卖新闻记者小俣行男的回忆(小俣《战场与记者》冬树社)。1942年有40-50名女性从朝鲜来到了仰光。听说开设了「慰安所」,要为新闻记者们提供特别服务,所以他(小俣)怀着非常喜悦的心情去了「慰安所」。然而,去了之后才发现,实际上为小俣提供服务的是一位23、24岁左右的女性,据说还是一位“公学校”(正确地说是1941年之后的初中在朝鲜也被称为国民学校)的老师。当被问到“学校的老师为何到这种地方来了”的时候,她回答说是被骗来的。这其实就是一种诱拐行为。
这位女性说,一起来的还有8名16、7岁的女孩子。她向读卖新闻记者小俣问到:“她们都哭着说不喜欢这种交易,有没有什么能够解救她们的方法?” 记者小俣考虑再三之后回答说:“ (叫她们)逃进宪兵队去求助吧”,“这些女孩子如果逃到宪兵队,或许对方能够为她们想出一些对策,当然也有可能反而受到处罚。但是,在现在的缅甸,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据说这些女孩们跑到了宪兵队求救,宪兵队也感到很为难,和「慰安妇」的老板磋商交涉的结果,最后8名少女被带到军官俱乐部去了。之后这些女孩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好像没有被送回朝鲜。那位原国民学校的老师又怎样了呢,结果是一直被拘留在「慰安所」,未获得自由。带他们去的业主也没有被逮捕,这种状况不胜枚举。
此外,曾经在新加坡为第3航空群燃料补给厂担任翻译的永濑隆这样说道:
“我曾经教过朝鲜籍「慰安妇」三次日语,她们知道我不是军人,所以把一些真话讲给我听。
她们说:‘翻译先生,实际上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工作是到新加坡的食堂里做女招待的。我们把当时得到的一百日元给了家人就出来了。谁知道到了新加坡之后却被命令去做「慰安妇」。’
他们带着央求的口吻对我讲了这些。但是,我只不过是一个翻译而已,根本没有力量去对抗军方的权力。我只是为她们感到可怜,心想:根本不应该用那种弥天大谎把他们骗来的。”(青山学院大学课题95编《青山学院与出征学生》私家版,东京都)
这种情况是诱拐和人身买卖并用的案例。
原宪兵队伍长畑谷好治曾经在对被带进中国东北珲春慰安所的朝鲜女性进行过人身搜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 我曾经故意岔开话题问她们‘你们知道是要做什么工作吗?’,她们几乎都回答说‘是为了慰问士兵’,‘我的歌唱得好,可以让那些士兵开心’等等。清楚知道自己要为士兵提供性服务的人很少。……这些女性们将从慰安所的老板或者“女衒”那里得到预付款之后交给自己的父母,或者直接由父母收取,由家里人的同意之后来到满洲的。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有正当的契约,但是她们无一例外地都说‘想尽早还清预付款,赚钱之后把它寄给父母兄弟姐妹’。”(畑中好治《远方的山河茫茫然》原名《遥かなる山河茫々と》私家版,京都市)
这也可以说是诱拐和人身买卖并存的案例。
关于朝鲜女性被通过诱拐或者人身买卖的形式征召的事实,秦郁彦也给予了承认。在他的著作《慰安妇与战场上的性》(新潮社、1999年)中,他列举了9例原军人的证言,只因“觉得可信度比较高而选入”。4例为朝鲜女性,其中3例为诱拐,1例为人身买卖(此外,日本女性中诱拐2例,强掳1例,在缅甸实施未遂1例,在新加坡的招募1例)
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我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据原宪兵曹长铃木卓四郎说,他从南宁慰安所的年轻朝鲜籍业主(地主的二儿子)那里听说,“契约上说的是在陆军的咖啡馆、食堂(里工作)”,这位业主才把当地的佃户的女儿带来的。他说“对强迫敬仰自己为“哥哥”的女孩子去卖淫这件事,他深感自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也有业主自身被欺骗的情况存在。这可以理解为军方的欺骗诱拐事件。
此外,关于在朝鲜是否存在由军方、警察实施的征召(强掳)行为,有受害者的诸多证言。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些证言的其他文书、记录和证言,但是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行为一件都不曾发生过。
1941年,为了准备对苏作战,军方进行了关东军特种演习(关特演)。以此为名义,进行了陆军总动员。此时,(军方)提出了征召2万名「慰安妇」的计划,其中多数的女性是从朝鲜进行动员的。当时召集的人数,据千田夏光从关东军参谋原善四郎那里听说的是8000人,而从关东军参谋部第3 课兵站班的村上贞夫那里得到的证言则是3千人左右(村上写给千田夏光的信,VAWW-NET Japan编《审判日军性奴隶制度的2000年女性国际战犯法庭记录》3卷,绿风出版,所收)。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秦郁彦所说的下述情况就是有可能存在的。“据说实际上只召集了8000人左右的妓女,但即便要在这么短时间召集这么多人,采用通常的办法是不行的。于是,就采用了道知事→郡守→面长(村長)这样逐级往下摊派的方式来进行。……我个人认为,实际情况正是‘半劝诱,半强制’(金一勉《天皇的军队与朝鲜慰安妇》)。”(秦《探寻昭和史之谜》)下卷,文艺春秋,1993年)关东军、朝鲜军、朝鲜总督府的相关资料多数已被烧毁,几乎没有保存下来的,如果能够有相关人员的资料出现的话,可能真相就会水落石出。关于这一点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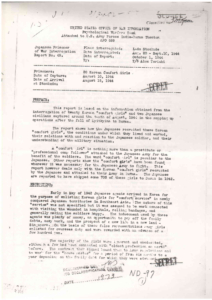
美国战时情报局资料



